秋水至,百川归河。泾流浩大,两岸渚涯之间,不辩牛马。泾流,浊流也。不辩牛马,水势广阔而岸远,使人难以一眼望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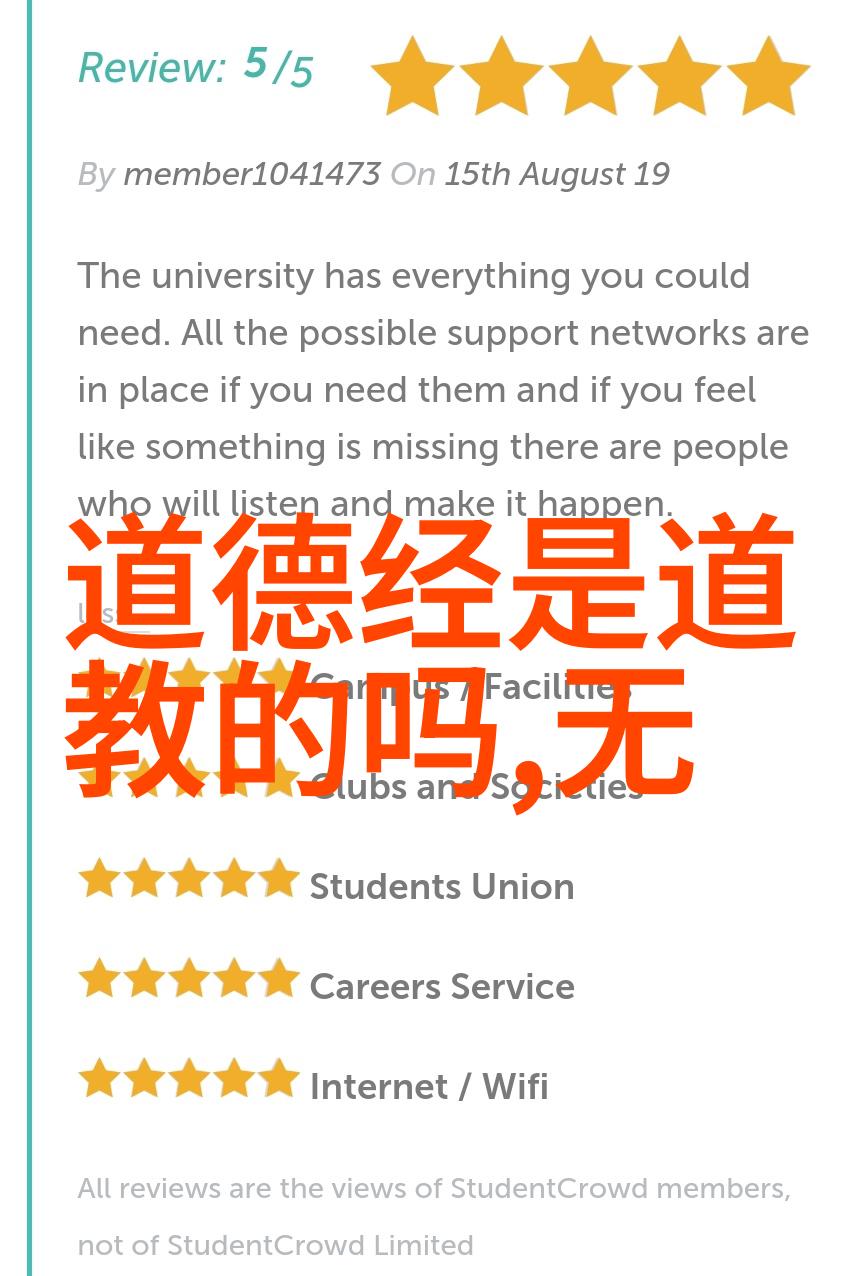
于是河伯自得其乐,以天下之美都寄寓于己。顺流东行至北海,对着海面而视,却发现水的尽头无法觅得。于是河伯转过脸来,看向北海若问道:
世间传言,有说百川皆我等可比拟者,我以为然。但听闻少仲尼轻视伯夷的仁义,我初时不信。今看子孙满堂之困难,我若非入门,便不足以免羞耻矣。我终将被大方家所笑。

北海若曰:“井中知鱼,但不知鱼出处;虚空但知空中景致,不知此乃地面上空。”夏虫不知冰冷,只是知道自己活在夏日;曲士只懂教条,不懂道路。这你从涯际观察到大海,这才明白自己的短处,你能与我讨论治理天下的道理吗?
天下之水,无一不归于大海;万川汇聚,其时何止?尾闾排放,其后何及?春秋四季常态,它们对洪荒和干旱均不知情。此其规模超越江河的流量,无法用尺寸衡量。而我之前从未因此自负,因为我把自己比作天地,用阴阳气象接受变化,我只是小石小木,在巨大的山脉间。我虽然有所见识,又怎样会自高?

计四海之在宇宙中的位置,与礨空石穴在大泽中的位置相似吗?计中国在世界的大范围内,与稊米在仓库中的位置相似吗?物体众多,我们仅居其中一人;我们生活九州,食物生长的地方、交通要道,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又是其中一人;这与万物相似,但如豪末般微不足道?
五帝连绵三王争斗,仁人忧虑任士劳苦,这些都是尽职了。伯夷辞官称名,而仲尼谈论博学。此即自鸣其盛,也不同于你曾经对水的理解。

河伯说:“那么,我是否太过渺小,将成为豪末?” 北海若回答:“不是。” 物质充满无穷,大智慧观察远近,因此事物虽小而不寡,大亦不多;洞悉数量的无限性。
证实古今永恒,以目光远眺而不会迷惑,以手捡拾而不会低头:洞察盈虚故能获得而不喜失去:洞察分界故能保持平静。当人们知道他们所了解的是极少,他们生命当场开始时更是不知道,从最微小寻求最大的领域,他们迷乱不能自立。这由此观之,又如何能确保豪末足以定位细节,又如何确保天地足以探究最大领域?

河伯说:“世上的议论者都说达到精妙则形散,无形不可围绕。” 北海若回答:“然而细看大者便无法完全领会,大看细者便无法完全明了。大致如此。”
精微、小巧,是形态的一部分。大器,小器,是容纳的一部分。它们各有各的存在方式。“精粗”指的是那些能够被数码捕捉到的形式,“无形”则超出了数码捕捉“不可围绕”则超出了数码追溯。“可以言论”的是粗糙的事物,“可以意致”的是精妙的事物。”
言语达不到深度意念达不到深度,所以自然就形成了“精粗”。所以伟大的行为是不出害人的,不多施恩惠也不贬低卑贱的人。不因利益动身,也不要鄙视门第的人。不争取财富,也不要多次辞让。不依赖他人完成事务,也不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过度工作也不贪污腐败的人行事特别怪异,但跟从众却又没有邪恶行为。他并不因为爵禄感到鼓励或因为羞辱感到屈服,他认识到了区分和选择之间没有界限,小和大的界限也不清晰。他听到这样的话:“道德高尚的人并非受命于民。”
约定分界线最后,最终已到达不能再分割、不能再讨论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就像夜晚月亮照耀一切一样,一旦白昼来临,即使有千军万马也难敌一枝箭毛蚁。如果有一切皆融合,那么谁敢承担起保护它们的手臂呢?
这就是一种“无方”,所有万物齐聚一起,有什么分别长短呢?这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开始结束,只有生死轮回,一切都随时间推移,而始终保持平稳状态。一点、一点儿都不停息,每个瞬间都像是新的开始。而且消息不断变换,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最终总会回到最初。但这一切变化都是根据自然规律进行,所以人们讲述这些宏伟故事和解释这些哲学原理也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运行规律。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纠结乎进退呢?毕竟我们将逐渐化为泥土。你只需坚守你的信念,不要忘记你的真实身份,那就是逆反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公孙龙问魏牟曰:龙年轻时学习先王之道,成熟后明白仁义礼让,这让我对于同类不同的理解更加周全,对坚硬柔软、黑白不同的理解更加深刻。不过我的思考是否正确,或许有人不同意,或许有人同意。但由于我的知识有限,而且我的词汇有限,因此我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接近真理了。不过现在我听到庄子的话语,让我感到茫然莫测。我不知道他的思想是否超过了我的水平或者是否差距悬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在说话似乎有些冒昧。我闭上嘴巴,没有勇气提出更多问题,请问他的理论是什么样的?
公子牟沉思良久,然后缓缓开口说道:"啊!吾闻君善通晓古今诸子百家之术,可共商奇策,此乃吾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