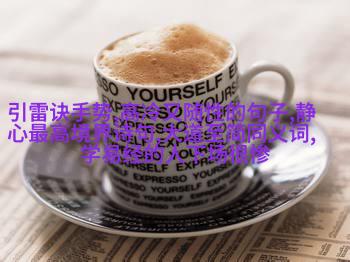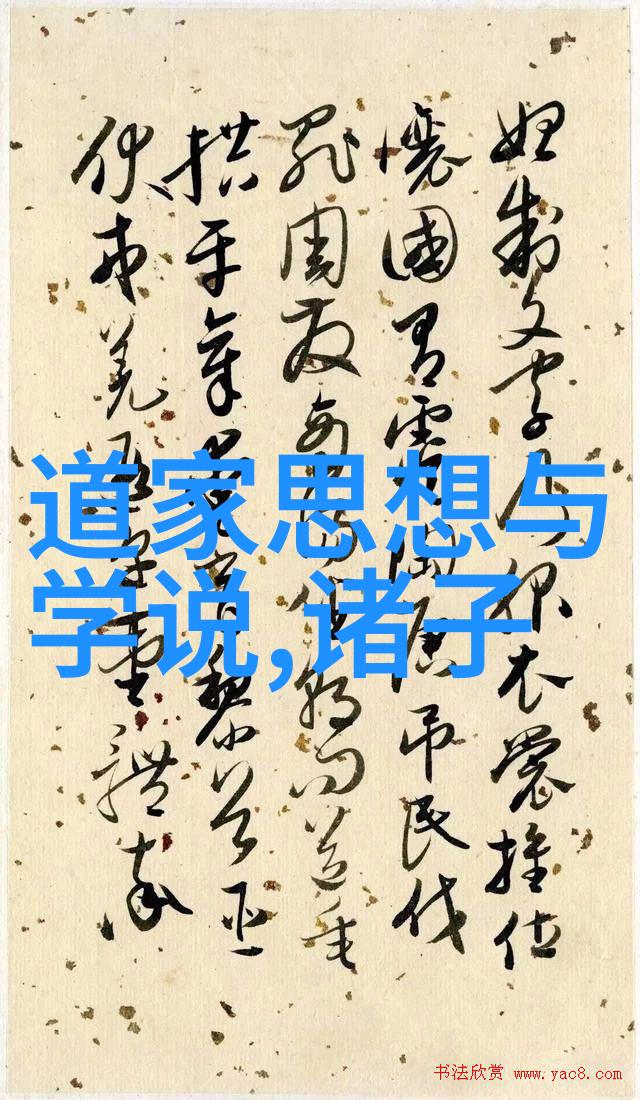科学与宗教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关系,犹如一场复杂的交响乐,每个音符都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们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普遍主义范式持批判态度,他们主张离开真理、确定性、普遍性、本质和系统的现代话语,并拒斥自由与宏大叙事。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变得尤为重要。

解构是后modernism的一种根本策略,它挑战了所有宏大叙述,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利奥塔提醒我们,这些宏大叙述不仅无法真正说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且为其合理性的辩护也正在衰落。这意味着包括宗教和科学在内的一切历史上具有主宰力量的“宏大叙述”必须从现代性的神坛上走下来,就像历史上的宗教世俗化一样。
然而,不同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如格里芬,他倡导一种建设后的modernism,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作为基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类型。他强调,我们需要超越“自然祛魅”,即否认自然有任何主体性、经验或感觉,而是要实现“自然返魅”,这意味着摈弃唯科学主义,但保留对自由、经验和理性的承诺。

尽管后modernism理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它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方式。美国学者巴伯提出了四种基本模式:对立、无关、中立整合。而后modernist分析方法,如视域融合,有助于深化这些模式之理解。
通过考察具体文化传统中的表现形式,后modernist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并非简单世界观问题,而是一种多样可能性涉及的问题。一方面,每门自然科目都有其差异;另一方面,每个信仰体系也是独特且不同的。这要求我们将问题转移到文化层面解决,使得科学家和神学家成为对话伙伴,同时尊重各自领域完整性,从而寻求新型整合。

这样的视角揭示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极端立场,如唯科学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神学。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实现一个新的共识,即支持后的modernist世界观,同时被后的scientific支持。这不仅展示了二者的全面改造,也揭示了他们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所扮演角色,以及它们如何被社会生活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所融入。
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过于简化,因为每一种信仰都是属于特定文化传统,但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此外,无论是在物质力量还是精神力量方面,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不可比拟的地位。因此,对于此类问题进行工具式处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人类文明仍需寻找基于世界观认识论意义上的共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