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循本卷之十六:探索社会中慈悲的最高境界

秋水至,百川归海。江水之广,两岸草木之间,不见牛马。江水,是浊流。不辩牛马,是因为水大,岸远,看不清楚。于是,河伯自得其乐,以天下之美为己有。在顺流而东行,一直到北海,然后向着北海看去,却发现没有水的尽头。于是,河伯转过脸来,用目光望向若神,并叹息。
“野语”有云:“闻道百川,都认为无人能及我。”这就是我的想法。但是,我曾听说孔子轻视伯夷的义,这让我不信任。我现在看到世间万物难以穷尽,我如果不是站在孔子的门前,那么我将会受到大家的讽刺和笑话。

北海若对河伯说:“井里的虫子不能谈论大海,因为它们被局限于虚空;虚空,就是井里所见到的空隙。”
夏虫不能谈论冰,因为它们太专注于季节;曲士不能谈论道路,因为他们太拘泥于教条。你从涯边观察大海,现在你才知道自己渺小,你将能够与我讨论宇宙的大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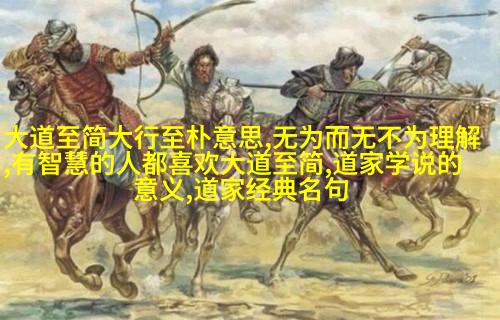
天下的所有水,无一比得上大海;所有的溪流都汇入它,但不知道何时会停止而不会满溢;它春秋四季永恒,而对于干旱和洪灾,它不知如何反应。这比起江河这样的流量,更无法衡量。而我从未觉得自己足够伟大,只是在比较自己与天地之间的情形,就像小石小木在山中的位置一样。我只是停留在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多做的事情呢?计算四面八方相对于天地来说,不像是那些落入深渊、空无一物的地方吧?中国虽然位于世界之内,但又如同稀薄的米粒堆积在巨大的仓库中一样。你数了数万物,却只占据了一片地方;九州的人民生活其中,他们生存的地方也是食物和交通线上的枢纽,也只占据了一片地方。这一切都是如此相似,与那些仅仅存在于马匹身体的一部分不同?五帝连绵不断,三王争斗不止,对仁德感兴趣的人也因此忧虑,对待士人也感到疲惫,这就足矣。伯夷辞让为名词,而仲尼用言语表达为博泛。此处所说的自负,不是像你一直以来那样对待水吧?
河伯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北海若回答说:“不要。”

事实上,大智慧来自远近,因此,小而不缺,大而不多;知晓数量无穷。证实过去便是当前,也遥不可及却不会感到闷闷或困顿:知晓时间终究有限。
通过观察盈亏,便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没有喜悦或忧愁:明白了时间终结与开始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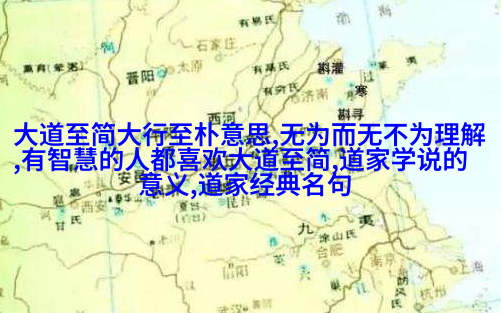
人们所了解的事务,不过是他们尚未理解的事务更加多样化,而且生命周期更长,以最微小寻求最大的极限,这就是迷乱并无法自立。如果这样看来,又怎样才能确定豪杰们能够决定细微事宜,又怎样才能确保天地充分掌握最大领域?
河伯问道:“世间议者都说达到精微则无形,或许这种理解合乎情感吗?”
北海道回答道:
凡事皆需反思,从细致到宏伟,从具体到抽象,从明了到隐晦,从可触摸到不可触摸——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许多东西,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宽广。如果我们要真正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这些简单的问题,要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思考生命、宇宙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等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考虑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水平很低,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正因为有这么些挑战,所以我们的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