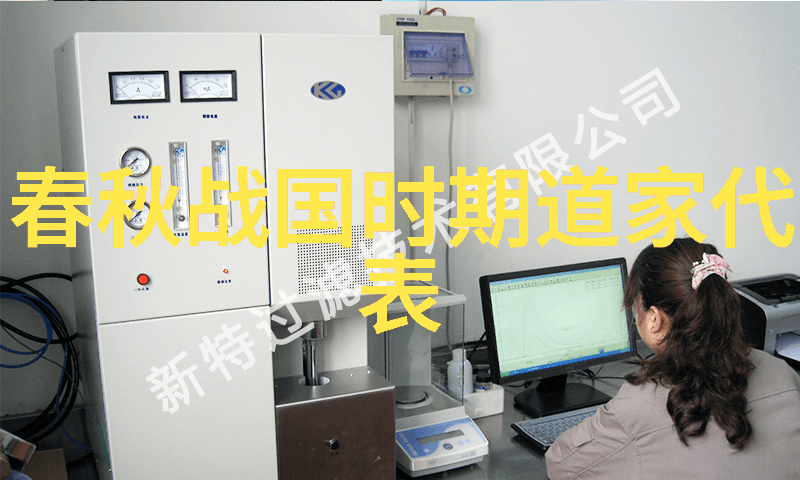在现代化进程中,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其民族文化传承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具有典型意义。然而,尽管凉山彝区是保存较多的彝族传统文化区域,但其民族文化传承仍然表现出“边缘化”的状态。

学校教育尤为体现这一点,如甘洛县胜利乡民族小学,其课程设置完全与四川汉区学校一样,没有关于彝族文化的地方教材或校本课本;教学安排与课时设计中完全依照通用教学大纲规定,没有关于彷觎族文化教育的安排。此外,全县共有8所学校开展彷觎语教学,其中7所为二类双语教育模式,1所为一类、二类双语教育模式并存,但实际上由于缺乏专职教师,大多数只安排1节,并且流于形式。
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缺乏必要了解,说彷觅语、懂得文的人越来越少,对于 彷觅 的历史、神话、风俗习惯所知甚少,一些独特文化传统如“克智”、“毕摩”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毕摩是社会宗教从事者,通晓文,是文经典的主要记录者和传承者,对本民族历史、神话文学等知识精通,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角色。然而近年来凉山毕摩数量急剧下降和传承堪忧。

此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极少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耗时费力的毕摩技艺,使得千百年的代代相传的毕摩文化面临失傳危险。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提高和意识形态领域松绑,有些曾经中断或原有的culture事项重新恢复或得到加强展现,这种情况被称为“复振”。
因此,“边缘化”的处境和“复振”的现象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如何适应并创造性地发展自身特色,而不至于在全球化潮流中迷失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岭光电土司提出的兼习两种不同Culture策略,即坚持自己的Culture,同时吸收借鉴他者的先进成分,以期达到既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又能适应主流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