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研究中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并于1984年出版了集结论文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这一提法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有识之士鲜少采用此称呼。与此同时,黄老之学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如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著作均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讲起,并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胡家聪、白奚及陈丽桂等人对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在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且我曾提及或考虑过 黄老道家的相关问题。

"黄老"一词,在文献中有其依据,《史记》中就有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言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于或归根于"黄老"。盖公善治黄 老言,而陈平本好以 黄帝、 老子的术。这类描述共计几十处,强调的是以 《 老子 》 为核心 的 道 家 思想,同时突出在之前加上了一个 黄帝。
随着关于 黄帝 的 传说 越来越多,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冠以"Huangdi jun chen ming"(皇帝君臣名)书籍,如 《 汉书·艺文志 》 记载,有二十七种这样的书籍,大部分可以归入 "杂而多端" 的 道 家 类别,这些都是由 道 家 人物创作,以 《 老子 》 基本思想为基础,由战国时的人根据 《 老子 》 而创作出来。近些年出土简帛材料中,也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属于 黄 老 思想文献内容大大丰富。

毫无疑问, 黄 老 之 学 是 一门 包容性的 学问,是 以 《 老 子 》 思想为 核心 的 戏法 中 心 集成 了 多 种 思 想 和 学问。这是 戏法 发展 和 包容性 突出的表现之一。当 时 尊崇古代先贤如尧舜而贬斥当今者,对此 道 家 拿出黃帝來,比尧舜更早,可以增强争鸣资本,使自己在儒释佛三教间更加具有竞争力。
西汉初年的当权者信仰并实践了Yellow Emperor's teachings,当时 Yellow Emperor's philosophy达到了巅峰,形成了一系列著作如Han Feizi(韩非子)的 Yellow Emperor' s Discourses( 黃帝內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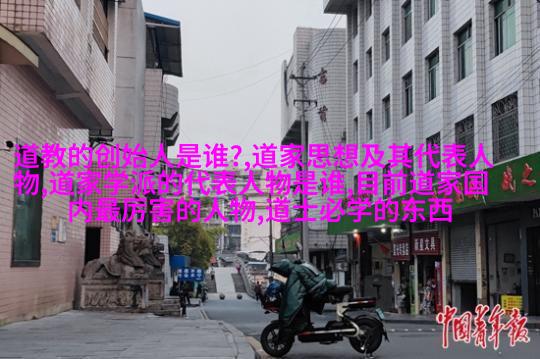
因此,“Yellow School”、“New Yellow Learning”,甚至包含 “Yellow Old Learning” 这样的用语,都应被接受使用。此外,由于其包容性极高,它能够不断发展并显示出显著发展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我将这个阶段称为 “Qin-Han New Daoism”。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国哲学简史里,将魏晋时代称为 "New Daoism”,他指出了玄学作为一种新的Daoist流派,与以前代表性的Lao-Zhuang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他解释称:“‘New Daoism’是一个新的名字,用来表示公元3至4世纪期间发生的事。”这反映了他对于Daoist流派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它持续创新发展的一致看法。我同意他的观点,或许我们应该将这个阶段命名为 “Wei-Jin New Daoism”。

通过历史时间段划分,我们还可以继续定义其他步骤,如唐宋期间可能会出现 "Tang-Song New Daoism”。每个步骤都承载着既定的历史意义,又包含着内涵上的创新意味。由于它们基于Laozi’s though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various stages and factio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ir roots in Laozi.
综上所述,将这些不同阶段命名如下:先秦,以庄周代表;战国-秦-Han,以Lao-Zhuang為中心;魏晋時稱為玄學,即「New Daoism」;唐宋後則可稱「Three Teachings Harmony」,即於自身立场主導下吸收融合儒學與釋教,這也是「Three Teachings Harmony」的體現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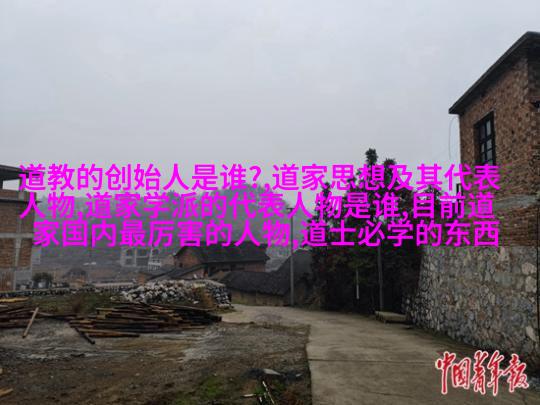
总结来说,“Qin-Han New Daoism,” “Wei-Jin New Daoism,” 及后来的各种形态(包括现代),这样的分类方式能体现出Daoist Philosophy及其文化遗产的一致性,以及它不断适应变化的心理过程。而且,它们能展示该体系如何包容其他文化元素,从而保持其活力和重要性。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系统化地描述和解释Daosim进程的话,那么利用这些名称提供一个框架,不仅能够清晰表达Daosim作为一种持续进化中的哲学,而且还能反映它开放包容他者的特质。“newness”正是在这里,其含义既体现在历史上的发展层次,也体现在内容上的革新与变迁上。而最终,这正是Daosim历经千年的生存与繁荣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