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述养生之要。先论顺其自然;后虽云养生,实视生死为一。吾有寿命有限,而知识无穷尽。顺着有限随着无限,岂不已矣?已而知之,岂不亦矣?善行莫近名,不恶远刑。依循天理,以道保身,以道全生,以道养亲,以道终年。

所谓近者,接近也;缘者,与也;督者,中也,如衣背缝间的裻衣取义也。善行必有美名,不恶必有惨刑,因此善恶忘却于心。不仅如此,对于善行无需追求美名,对于恶行无需避免惨刑,这样便能超越了名与刑的束缚。但须将这理念铭记在心中。
老子所言“中”是抱持一体守住中的中心,不是指夹在善恶之间的中间位置。这一点朱熹《书皇极辩》批评过,但未必真正理解其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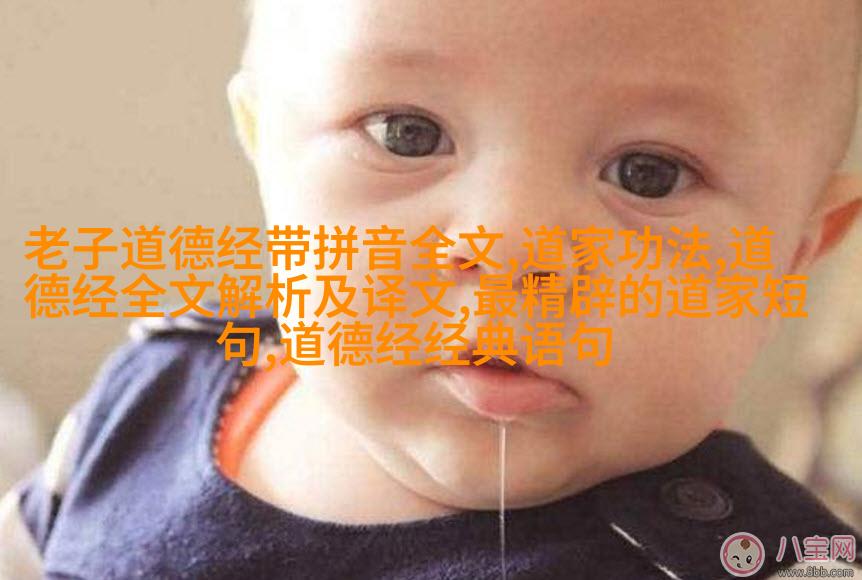
庖丁解牛,为文惠君解牛演示喻世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的手触及牛肉、肩膀靠依牛体。他用力时肩膀倾斜。他脚踏在地、膝盖蹲下,用膝骨支撑地面发出声音,就像音乐般响起,有节奏如同演奏乐器一样完美协调,无不符合桑林舞曲和狸首节奏的律动。
《左传》注释说桑林是殷商时期的乐曲,《礼记》则提到射艺诸侯以狸首为节。此处讲的是庖丁解牛与两种古代乐章相似,都涉及至神秘又深奥的事物。文惠君赞叹地说:“嘻!音高昂,其声舒缓,是不是技艺到了顶点啊?”庖丁回答说:“我喜欢的是这个刀法,它已经达到了艺术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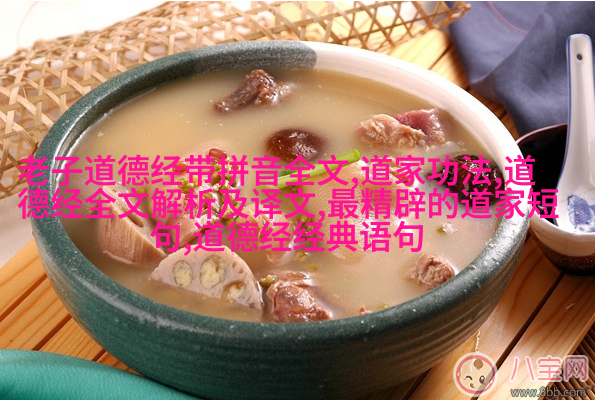
始初,我解牛时,只看到牛肉和骨头没有别什么;三年之后,再看就只剩下空壳;现在,我可以用心感应而不用眼睛看,用官能止住而神欲行动。我只凭借天定的规律去处理这些自然现象,没有刻意观察,也没有主观判断,只顺着自然规律去做事。
开始每次割肉都感到困难,但随着时间积累,每次都能更精确地切割到筋骨之间,从未出现过误伤的情况。而且尽管我的刀已经使用了十九年,比起最初使用的时候还更加锋利,这说明我的刀刃虽然很薄,却能够穿透那些空间间隙,使得每一次切割都留下余地,所以即使经过十九年的磨损,也仍然保持原来的锋利程度。这正是我所坚持的一种生活态度,即使再小的事情我都会认真对待,因为我知道这是维护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文轩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庖丁回答:“因为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公文轩听后感叹说:“你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些养生的道理。”
接着他反思自己虽然擅长使用刀具,但是每当要进行大型工作时,他就会感到紧张不安,因为他知道那将是一个艰难重大的任务。在过去,当他的手不会这样稳定的时候,他会感到恐慌,现在虽然技术上进步很多,但是行为还是显得迟缓。他把事情推给了其他人,说自己能力不足,并且总是在四周寻找帮助,看起来既充满期待又显得有些犹豫,这样的行为让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并不平静,并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感觉到失落和沮丧。当事情结束之后,他会欣赏自己完成工作的情景,而非实际过程中的挣扎和挑战。但这并不能改变内心深处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更多挑战的心存忧虑。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类情感反应,它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基本关怀,我们渴望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通过学习如何更好地管理我们的身体以及如何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来达到这一目标。

老聃去世后,有人为其吊唁三次,然后才离开,被认为是不敬之举,他们质疑那个人是否曾经是老聃的朋友。那个人回应说: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友谊,那么连死讯都不值得悲哀。但若真是真正朋友,那么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如果真的是老聃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
这段故事强调了人类对于死亡及其意义的一种普遍忽视,以及我们往往因为害怕或无法接受死亡所以选择逃避它。而根据古人的教导,我们应当学会接受死亡作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能够更加珍惜生命,同时也不再被死亡带来的恐惧所左右。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死,所以哭泣或哀悼似乎都是多余的事情。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让我们认识到生命短暂,我们应该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以及如何面对最终不可避免的事实——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