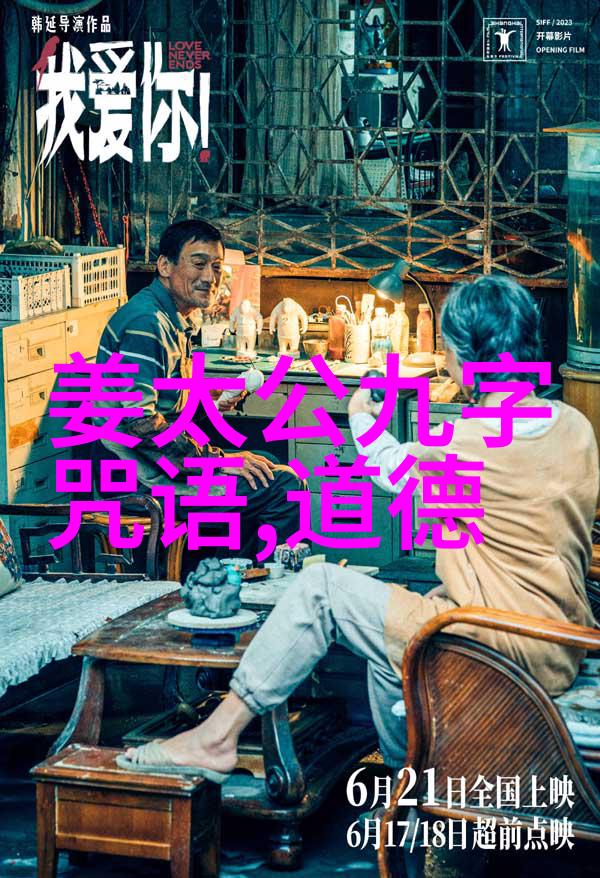此篇述养生之要。先论顺其自然;后谈虽云养生,实则视生死为一。吾有涯于生命,而知无际限。在有涯随无涯,已足矣;已而知之,亦足矣。善行不求名位,恶行不逃刑罚。顺天自然法,可以保身,可以全活,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近者指接近之近。缘者谓顺也。督者中也,如衣背缝中之裻,以取此义。不仅善行必得名誉,不仅恶行必遭惩罚,更能忘却善恶二字的分别。而若言其善,则无需追求名声中的美好;若言其恶,则无需避免刑罚中的祸害,因为既超越了善恶的界限,也脱离了名利的牵绊。但必须将此作为常理坚守。
老子所说“中和”,抱一以守中,又非指夹在善与恶之间的位置,而是指一种状态,即保持内心的一致与平衡。这一点朱熹在《皇极辩》后对其进行批评,但未必完全理解老子的本意。

庖丁解牛,为文惠君解牛而作喻,用刀手触、肩依均恰到好处,却又力度适宜,不至倾斜。此乃养生的道理之一,其妙处在于动作轻巧如同奏乐一般,每一个切割都恰到好处,无一不符合桑林舞蹈和狸首节律的要求。
《左传》注云:“桑林,是殷王朝时乐。”《礼记》曰:“射义,以狸首为节。”又云:“狸首砉,是乐会时也。”这两种乐章,都源自解牛的场景,其中汤王祷求桑林,用身体做祭品,诸侯歌唱狸首以示射击没有回应,这些都从解牛的情景得到启发。

文惠君赞叹道:“嘻!音熙叹声,真佳!”庖丁回答说:“臣所喜爱的是刀法本身,它已经达到技艺的巅峰。当初我开始解牛时,只看到牛肉,没有看到整只牛三年之后,再看也不见完整的牛体,现在我用心感受,而不是眼睛观察,我知道止步,但我的神意还想继续前进。”
目不能见远,就像天命一样自然而然地分配给每个人,有的人才能独特,有的人却不得独特,这就是由天定的安排。如果你问他是人命定或者天命,那他会告诉你这是由天定的,并非人的选择。他自问自答地说:“这介士出自天,不是人间造物。他(介士)应该有双脚相互依靠,但现在只有一个脚,所以他来自于天。”

就像泽边雉鸟每十步啄食,每百步饮水,没有目的地只是生活,而且即使神灵拥有力量,如果它们被困在笼子里,也不会感到快乐。这说明即便是最高级别的地位或权力,如果局促不宽畅,也不会感到满足。这也是失去了养生的智慧所导致的问题。
老聃去世后,被秦国读书人误认为是一位佚吊三号并出门询问是否他的朋友,当被告知确实如此,他就责怪那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这样哭泣,因为如果真是他的朋友,那么应当更加悲痛才对。但这个读书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最终意识到了自己过分世俗化的情感反应,与古代人们遁逃自然规律、违背真情、忘记接受命运赋予的事业和责任相悖,从而成为逆逆天罪孽的一个例证。

适来适去,对应着夫子的教导,当事物按顺序发展,我们应该安然接受,这样我们就能享受生命带来的喜悦,而死亡也变得平静可容忍。这正如帝王治理国家,使阴阳五行合成万物,让人类根据这些规律生活,从而获得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如果我们能够像帝王那样治理自己内心世界,那么一切烦恼都会消散,因此这种方式被称为“帝县解音玄”。
上古时代的人们因为懂得这一原则,所以他们可以安然面对生死变化。在那样的时代,他们虽然也有欢笑和泪水,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过去的事情,一旦结束,就再也不复返。而我们现代人往往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的教育应该从这里开始,将这一哲学融入日常生活中,让人们学会如何更好地珍惜生命,同时准备迎接死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