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述养生之要。先论顺其自然;后谈虽云养生,实则视生死为一。吾有涯于生命,而知无际限。在有涯随无涯,已足矣;已而知之,亦足矣。善行不求名位,恶行不逃刑罚。顺天自然法,可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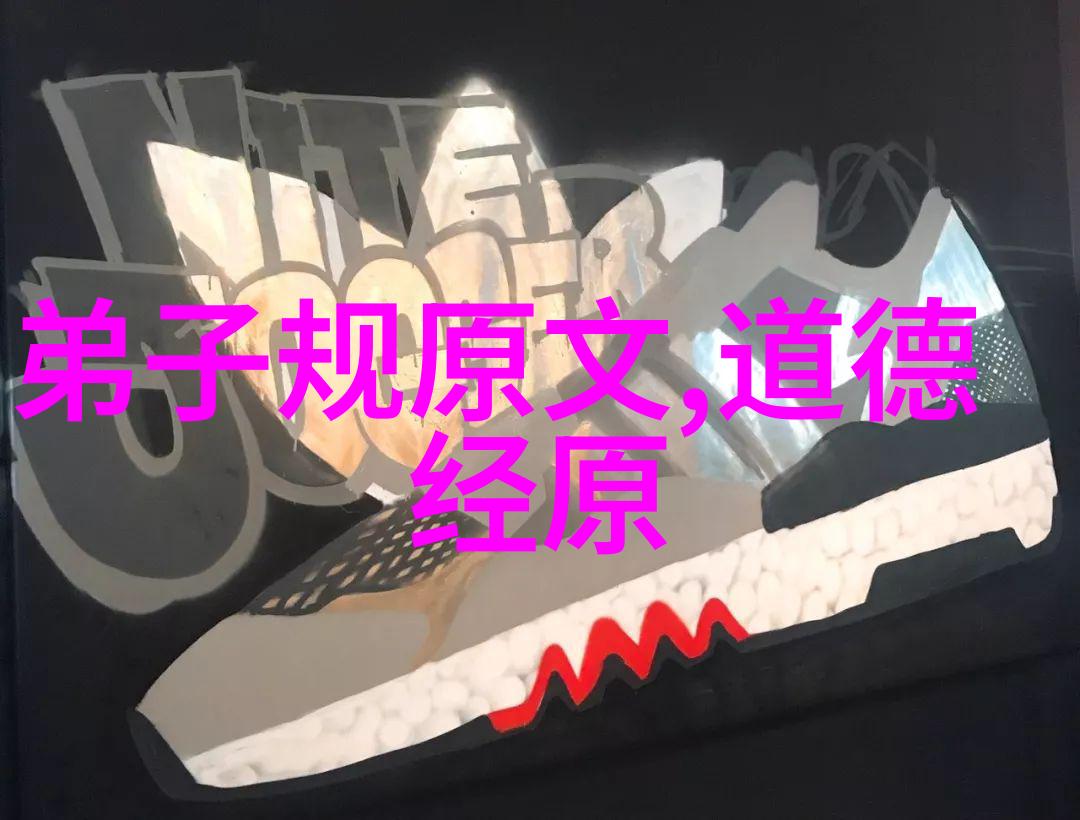
近者,即邻近之近也;缘者,即顺也;督者,即中也,如衣背缝间的裻衣所取义也。为善者必有名声,为恶者必受刑罚,但善恶两忘,此乃无为而治之道。但吾心中以为常。
老子所言中的道,不是夹在善恶之间的道,也非朱子所谓的极辩后非。庖丁解牛于文惠君梁惠王前,其手触处肩倚处,便见其用力过猛,使肩斜了。

每步踏地,每膝压地,都伴着微小的声音,一种悠扬和谐的声音,就像奏乐一样,有节奏,有韵律。而这声音,是可以听到的,只需轻轻一提刀,就能听到那清脆的响声。
就如桑林舞曲,与《左传》注中的狸首相合,那就是乐会时刻。这两种乐章,用来比喻汤时祷请桑林以身为牺牲,以及诸侯歌狸首以射首不朝,这些都来自解牛的事例。

文惠君赞叹曰:“何等高兴!技艺到了这个境界吗?”庖丁回答说:“我喜爱的是这一条道路,它超越了技艺。”起初,我解牛时,看去只有牛肉;三年之后,从未看到完整的牛体;现在,我依靠天理而不是眼睛看待身体,把它分开成部分,每个部位都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地方。我没有用力切割,只是让刀锋自在地穿透,无须努力地磨损刀刃,以至十九年后的今天,这把刀还是刚从磨盘上削出的样子。
彼时节奏间隔很大,但刀刃却非常薄,以这种薄弱进入那些空隙,让人觉得它们游刃有余。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使用了十九年的时间,这把刀仍然保持新锐锋利状态。不过,每当我准备进行下一个动作,我都会感到困难,然后立即停止,并且变得犹豫,因为行为慢得令人不安。当我开始使用刀的时候动作非常微妙,但已经能够感觉到已经开始分解的情况,就像土壤被抛弃的地面上提起我的手持武器,对周围环顾四周,对自己踌躇满志,因为我掌握了一件优秀的工具并将其妥善保存起来。此事对您来说又有什么可疑吗?您是否认为这是人工或命运决定呢?

公孙轩问:“你究竟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如何?”他惊讶地说:“你怎么这么做?”他继续质问:“你是出于天意还是人的安排?”
庖丁回答说:“这只是因为人们必须独自生活,而不是因为他们双脚齐平。”这样,他指出了自己的独特性格,并暗示自己并非普通的人类。他接着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应该知道这是由天定的命运。”

接着,他用鸟啄食和饮水来比喻他的观点:雉鸟在泽中自由地觅食与饮水,不需要任何栽培或关怀。如果它们被囚禁在笼子里,即便神仙照料也不足以充分享受自由生活,因此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他再次强调“独立”是一个重要原则,在追求真理和知识方面,我们不能依赖外界因素,更不能接受世俗情感干扰我们的判断。
最后,他引用老子的故事来说明他的观点:秦佚曾经向老聃询问是否朋友,当老聃三次号哭后出来时,秦佚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误以为秦佧是一位学士,却发现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古代,他们遁避世俗情感,用一种超脱的心态面对死亡和哀伤这样的现象,他们明白真正重要的是遵循自然规律,不被情感束缚,从而达到一种超脱与平静的心境状态。这正是养生的根本意义所在——理解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一致性,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