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充於内,物应於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鲁有兀者王驸,姓王名驰,鲁人也。刖一足日兀。形虽残兀,而心实虚忘,故冠《德充符》而为篇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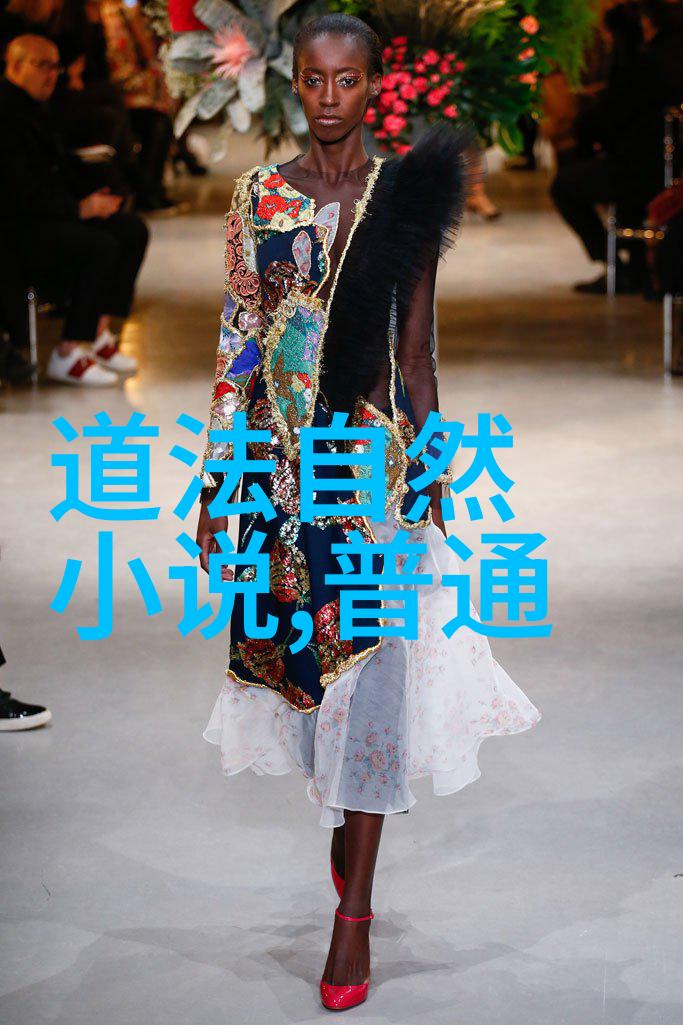
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
注:如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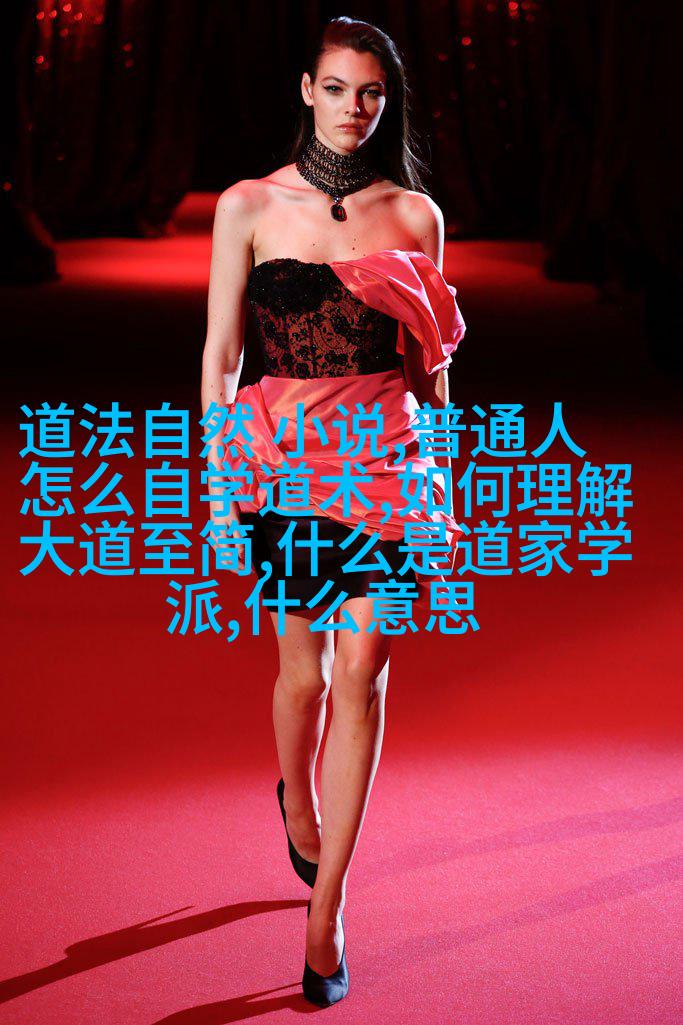
疏:陪从王聆禀学,门人多少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问於仲尼曰:王驸,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

疏:姓常名季,是位居鲁国的贤士;王聆是位拥有盛德的人,他的形体虽然残缺,但心境却非常宁静和淡泊,因此他能够跟随并学习孔子的教义。
立不教,坐不议,无言而往,无事而归。

注:各自得以满足,不需要多言或多事。
疏:“立”、“坐”指的是站立和坐着,“不教”、“不议”意味着没有进行教育或讨论,“无言而往”表示在行动之前不会有过多的言语交谈,“无事而归”则是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带回任何烦恼或问题。这反映了一种超脱世俗纷扰、专注于内省修养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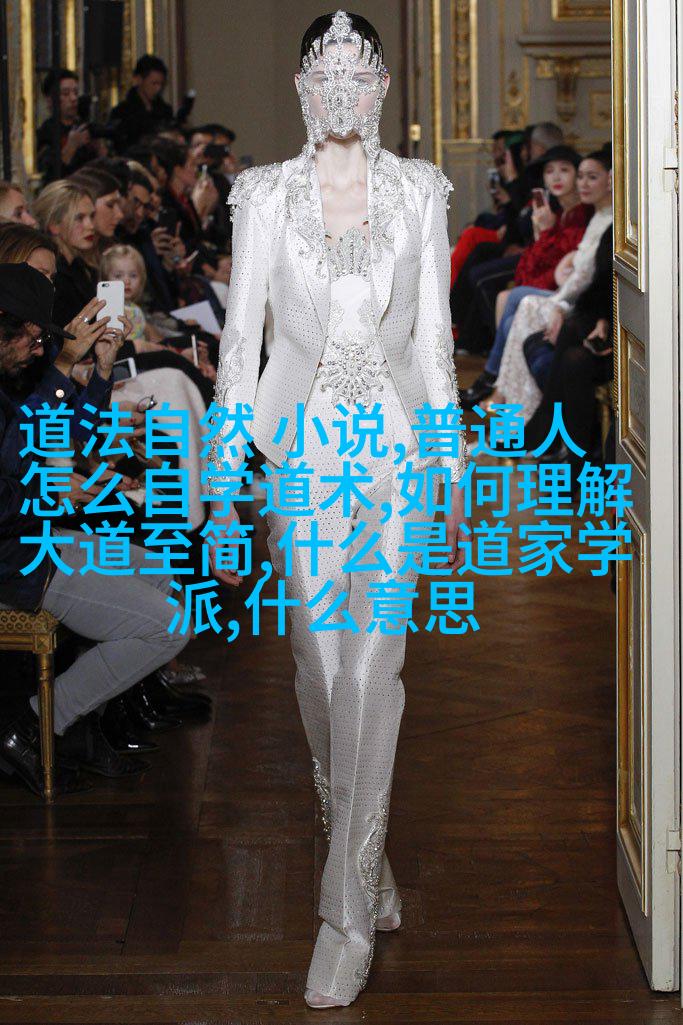
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残形而心乃充足也。”
疏:“教授门人”,即孔子对他的弟子进行教育“曾未曾讲说”,表明他们并不依赖于口头上的解释或者辩论,而是通过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来体现自己的道德标准。“请益则虚心而往”,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保持一颗虚空的心去迎接挑战,“得理则实腹 而归”。因此,他们既不会因为知识的不足感到不安,也不会因得到答案后的满足感让自己停滞不前。在这过程中,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被外界的事务所牵引,这正是“无为才能无所不为”的精神状态。
这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残兀然而聚众极多。”他对此感到好奇,因为尽管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很差,却能吸引如此众多的人跟随。他想探究这种情况背后的道理,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仲尼曰:
夫子圣人也,我直后且未往耳。我将以为师,而况晚学之徒乎?
疏:“宣尼呼王聆为夫子”,这里的“宣尼”指的是孔子的学生之一,即“宣”的弟弟,由此可知他与孔子的关系相当亲近。而在回答常季的问题时,他用了一种谦逊但又自信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还没达到完美境界但已经走过许多路的人,对待这些晚来的追随者应该怎样看待?
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与从之!
注:“夫神全心具,则体与物冥。”
疏:“奚”,何也不必局限于一个小地方,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吸引整个世界来跟随我的道路。”
常季曰:
彼兀者,其与庸亦远矣。
疏:“庸”,常也是个字典里的意思,它代表了稳定、平凡,但在这里它可能更多地象征着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或者共同点。在这一段话里,可以理解成有一种距离感,那就是由于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认知导致的一种自然隔离,使得那些更深入理解的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