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梅花即将盛开之际,我再次踏上了离别的路。冬日的北京,雪花未曾飘落,而林海音在口中的“骑着毛驴儿逛白云观”的场景,如同梦境般消失无踪。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住在庙里的道长正忙于准备庙会,这一年的春节倒是异常热闹,一位南方人第一次见识到了如此热闹的人潮。

在车站与朋友告别,我们并未多余时间相聚,只有新年这一次的短暂相遇便是在离别的车站中。我送给他半年前托付的小像,并附上一个平安符作为新年的祝福和祈愿。他笑着收下,将其放在最里面的口袋里,然后告辞,他要去广西学习绘画。在十分钟后,我们再次面对,眼眶湿润地说了再见。
天南海北,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能坐在一起好好交流。每一次匆匆赶场,都仿佛是一场梦,但又实实在在地体验了奔波劳苦的一年又一年。在回家的路上,我带了一本小说,其中有一篇《夜车》,提到南拳妈妈歌曲:“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回到家乡,每个除夕晚上,全家围坐在一起分享一年来的收获,无论顺逆,都抛诸脑后,最终只剩下一句祝福和感慨,最幸运的是大家都平安健康地团聚在一起。
家乡的年味并没有那么浓郁,也缺乏暖气,让我如同旅客一般,在这里停留。而实际上,无论何处都是短暂落脚,直至归根结底,才明白自己一直在奔波游荡,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与最初的地方越来越远。韦庄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夏夜里,我总能听见水声,那是河流的声音。如果在地图上标注我曾经行走过的地方,便发现一切缘起都沿着这条河流,这是一条明晰线索。当我走向它时,那些记忆似乎仍旧存在,就像那条河流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澈明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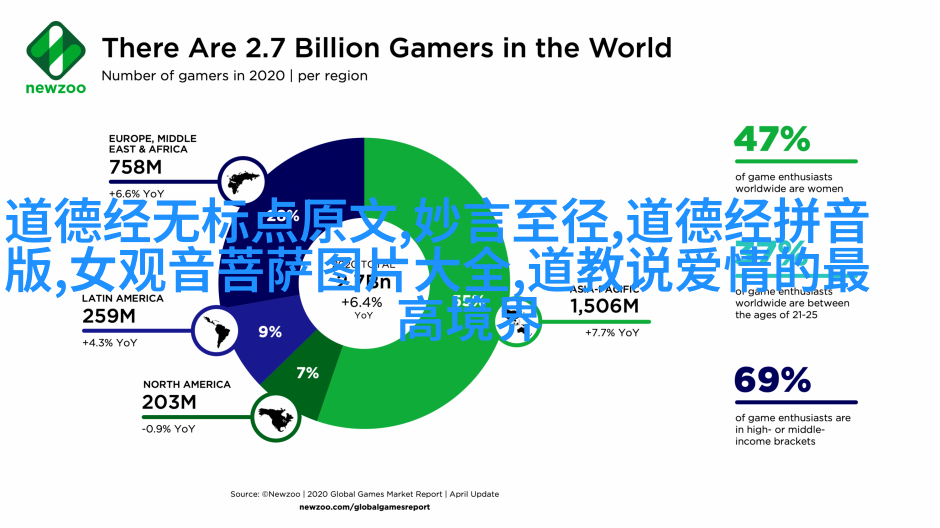
这一年的“浪迹”真是漫长,有机会见识了各种人,每天想去白云观,却恰逢它最热闹的时候离开返回南方。回京时,当最后一天庙会尚未结束,我看到太阳照亮邱祖殿的一个道长正在窗台写字,即使立春已过寒意犹存,他们却已经习惯于这个无空调殿堂度过整个冬季,让那些生活在温暖室内的人感到惭愧。
哲学课上的老师常引述赫拉克利特的话:“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物变化之大不可测三毛在丹纳利芙群岛上看到画作,对杏花烟雨江南产生怀念,但她生命中的旅行从未停止,她说,“不要问我从哪儿来,我的故乡就在远方”,此后的回望仅存于梦中,当时画里的避秦者与她隔绝千山万水。此后的追寻只存在诗歌中。当高晓松唱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有人则提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和后天的苟且”。无论如何,要成为真正的人,不管漂泊何处,都要保持初心,把每个避风港视为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