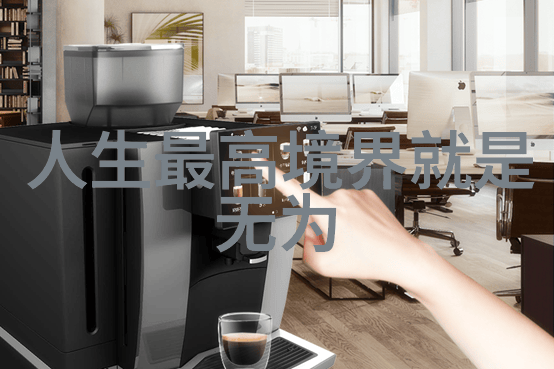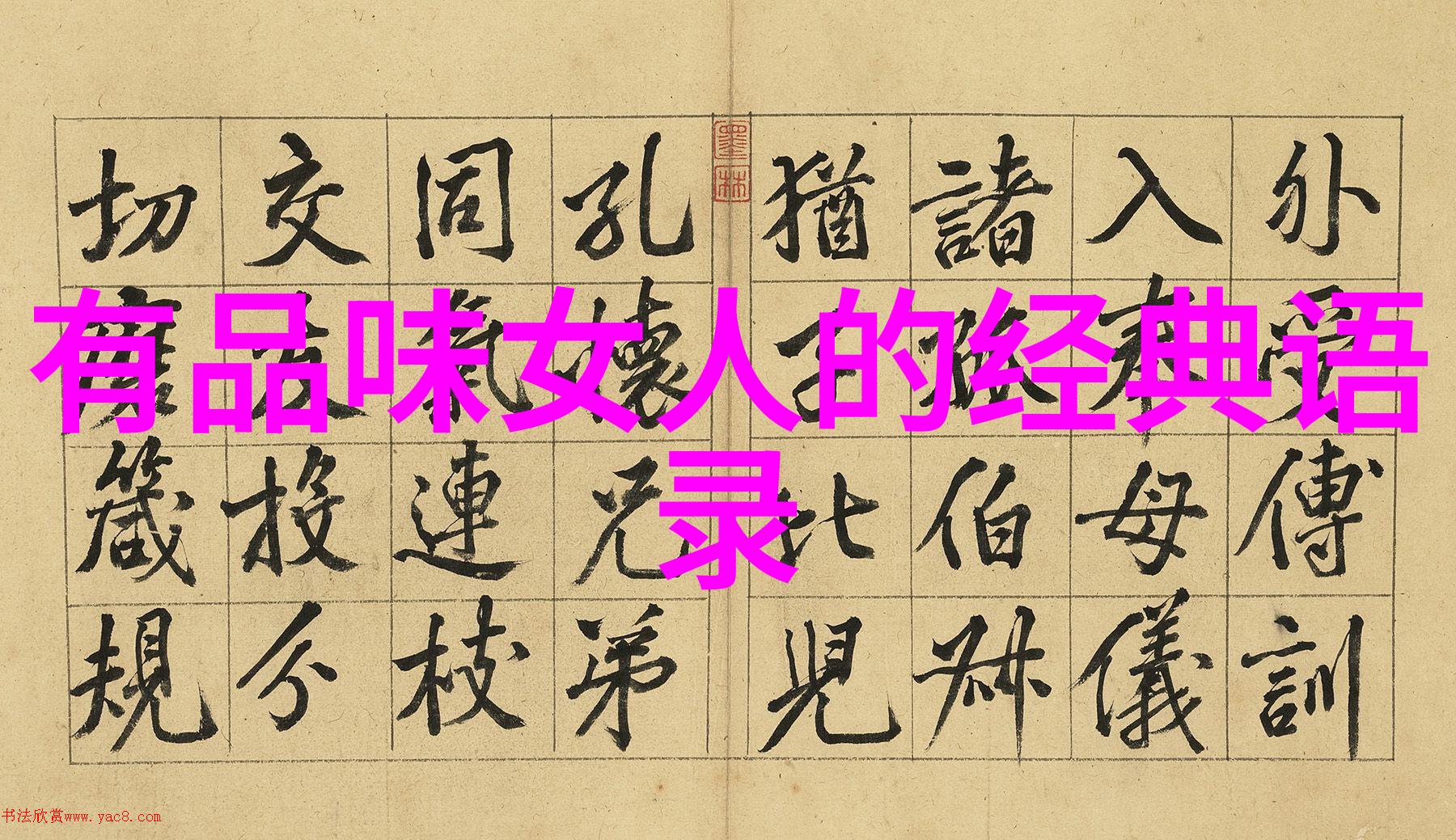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的争论中,经过出家僧人和信佛士大夫的反复解释,终于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佛教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信仰多神教的国家,一般倾向于一种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佛教、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也曾传入,均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人在宗教上是一种“混血儿”。 多神信仰影响下的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上。中原的统治者想把周边的少数民族变为华夏,向落后民族传播先进的礼乐文化,即是“用夏变夷”。但是这种传播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依靠边裔四夷向中原文化的自觉靠拢。孔子在上提出了以“修文德以来之”为纲领的民族和平同化政策。儒家“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诸民族自愿归附的文化中心,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盆地”现象。我国古代的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历史上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也不少。但是宗教并非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物质利益的争夺才是民族冲突的本质。而且我国古代民族冲突的结果不是民族的分崩离析,而是在每一轮重大的民族冲突过后,都有一轮更高层级的民族融合。这种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侵入中原,而且有时候还会长期驻扎下来,建立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方王朝或者中央王朝。可以说,我国古代地理范围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是这种文化吸附的结果。 毋庸讳言,我国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矛盾,当矛盾尖锐的时候,也会发生民族冲突和战争。但是从整个历史看,冲突和战争是短暂的,和平与融合才是常态的。因为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信仰、利益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即使面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化、瓦解,这除了中华民族自身拥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外,没有因信仰因素造成的离心力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