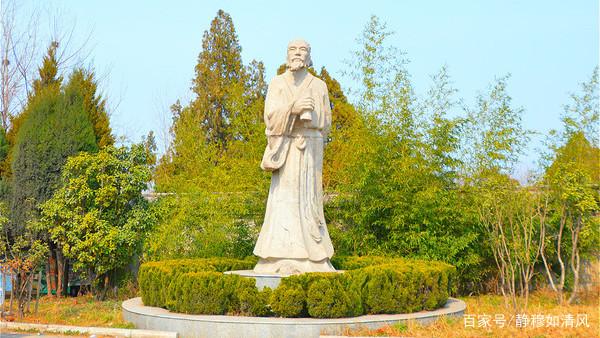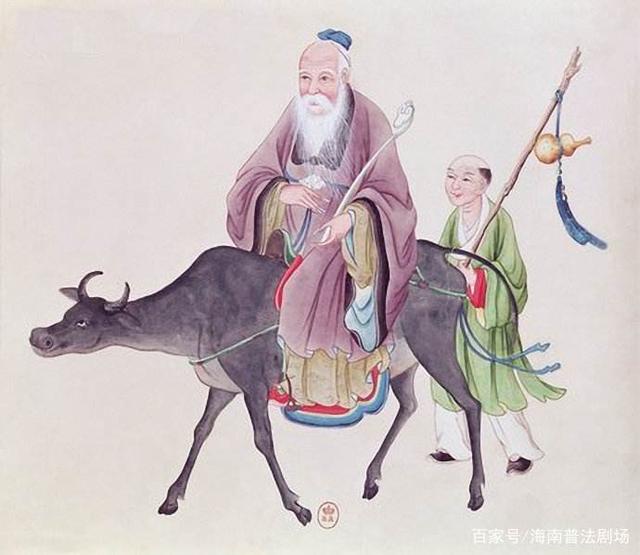道家故事里,唐开元九年,大唐王朝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举行着一场隆重的授箓仪式,唐明皇李隆基成为了一名道士皇帝。而那位授箓的道士,正是宗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出生于河内郡温县,尽管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但他不喜为吏,却是个勤于学习、热爱道教的好青年。21岁时,他入了道教圣地嵩山,跟随上清派宗师潘师正学习上清经法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技术。他对学道充满热情,为此,他曾经在读经的时候,放了一百片瓦砾在案头作为鞭策。道家故事里讲述,当年司马承祯用移瓦片当作读经的标记,在案头每日读书上百卷。经过勤奋学习和数位名山访道后,司马承祯在浙江天台山结庐定居,被称赞为“白云子”。他的人品和学术成就非常高,多位皇帝曾诏请他入京,请求他指点迷津,并被尊为帝师。武则天也曾亲自降制状和他交流。一次,睿宗李旦请司马承祯入朝,询问他关于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的问题。司马承祯借助老子无为之思,详细阐述了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旨和身、国同治的道理。睿宗深表赞许,并体现这种精神,禅让皇位给了儿子李隆基(即唐玄宗)。但是,当被邀请留在长安辅佐朝廷的时候,司马承祯婉拒了,并请求回山。皇帝很了解他的音乐才能,遂赐赠他宝琴等物,并特意为他写下了表彰的文章。道家故事中,卢藏用曾隐居于终南山,后来官拜要职,被人称为“随驾隐士”。听闻司马承祯将要回天台山,他向司马承祯指着终南山,询问他为何要走这条“绕路”,司马承祯幽默地回答:“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山便成了“终南捷径”的典故。司马承祯并没有意图辅佐政府,然而睿宗多次邀请他,才让他离开山林入长安。但他离开不到十里便后悔了,于是留在司马悔山(今天台山北),成为了道教第六十福地。唐玄宗信仰道教,与司马承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道教的发展,这使得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首先,他提高了道祖老子的地位,尊《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为之作注。其次,他对道教进行规范,设“道举制度”,并以“四子真经”(即《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科目来选拔人才,这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支持。道家故事中有这样的情节:唐玄宗授箓给司马承祯之后不久,他便请辞还天台山。玄宗以诗表达了对司马承祯高蹈出尘之风的赞赏,并流露了对他的不舍之情。为方便以后召见,玄宗命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敕号“阳台观”。司马承祯偏爱王屋山,除了地处故乡之外,还因为这里没有像终南山那样的游人和隐士,也不像嵩山那样有很多的佛寺和道观。在这里,他可以享受到“山林寂系”的清幽和寥廓。不久,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也前来拜师修道,王屋山的道风因此备受推崇。司马承祯以“天地宫府图”为名,特别将王屋山列为“清虚小有”的天,并称它为洞天福地之首。他在前人基础上,将道家的“洞天福地”说系统化、理论化,将分散各处的道教遗址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为中国道教史上被后人称赞为杰出贡献。在那里,他还建了崇玄馆、设立玄学博士等一系列教育机构和职务,为王屋山的道教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道家故事中有这样的情节:唐朝时期,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开创了洞天福地的整合说,将各地散落的道教遗址规范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形式,创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加以发扬,进一步推动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开元十二年(724年),司马承祯再次应唐玄宗之召入京讲授上清经法,深受玄宗的厚爱。司马承祯曾请求一事,玄宗即敕五岳山各建真君祠一所,由司马承祯主管祭祀。这使得道教获得了参加国家重要祭祀的权利,大大提升了道教的地位。这一事件被誉为道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直被后人所铭记。
司马承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坐忘论》《服气精义论》《天地宫府图》等,皆被道教类书《云笈七笺》所收录。其中,《服气精义论》详细记录了几种服气的施行步骤和方法,探讨了服气养生与治病等问题,成为道教养生和健康疗法的重要指南。而所谓“服气”,又称为“行气”“炼气”“食气”,是以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内修功夫为基础的一种养生方法。司马承祯在他的著作《坐忘论》中进一步概括阐述了道教理论,对道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故事中有这样的情节:司马承祯是一位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的著作《坐忘论》是神仙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坐忘一词,源自《庄子·大宗师》,意为外忘身体,内忘心志,达到一种灵与肉分离的境界。司马承祯以道家经典《老子》、《庄子》为基础,综合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的禅定、止观等思想,提出了修行的核心思想“守静去欲”,并围绕这一思想将修行分为7个步骤: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7个步骤也是修行者的7个阶次,每一阶次都比上一阶次更高,直至达到最高境界——得道。
在隋唐时期,道教的外丹派别仍然十分盛行。然而,司马承祯认识到外丹术的弊端,并开始大力倡导修心明道、精神心性等实践方法,从而进行了一次思想转型。他的“守静去欲”的心性理论不仅引导了道教重心的转移,也使得早期道教的物质之注重和重玄清谈的风气向具体的宗教实践转变,从单纯的以炼形为主发展到注重身心一体、性命双修的阶段。通过这一思想转型,司马承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教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道教思想的内涵,为后来的道教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道家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司马承祯是一位全能型道士,既是一位道教理论家,又是一位艺术家。他不仅著述了众多道教经书和经赞,还涉及诗词文赋、医药本草等领域。司马承祯擅长篆、隶书,他的书法被誉为“金剪刀书”,曾受到玄宗的嘉奖。玄宗还曾让他用三种书体书写《道德经》,并定著为真本。不仅如此,司马承祯还擅长制作铜镜、宝剑、琴等器物。一次千秋节,他献给玄宗一枚八卦纹镜,备受玄宗重视。玄宗为这枚镜子御制了一首诗,称赞八卦纹镜“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正是对司马承祯扶正除邪的高度评价。
司马承祯的多才多艺不仅让他在当时备受尊重,也让他的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学说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道教,还影响到了后来的宋代内丹学。他所倡导的“守静去欲”的心性理论,为道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司马承祯不但在理论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艺术领域也展现了出色的才华。他全能的艺术天赋和高尚的道家气质,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展现出了道家思想与艺术的卓越结合。道家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司马承祯一生辞书、弃官,投身于道教学问的探究与实践之中,并创立了自己的修行理论。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精通书法、制作工艺和音乐等方面,在当时备受推崇。司马承祯的离世可谓是落寞而又高尚的。当时正逢玄宗经历了安禄山之乱和削弱禁卫军力度等事,朝廷对道教也开始存疑。然而,司马承祯依旧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毫不动摇。在王屋山去世时,享年89岁,被玄宗封赠为银青光禄大夫,谥号为“贞一先生”。他的学生和崇奉者不乏道门中坚,他的理论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道教发展。司马承祯一生注重内心修行,踏实地追求自己的信仰,成为了道家思想与实践的典范。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唐朝,如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司马承祯的地位显得愈发重要。他丰富了中国道教的内涵,让道教学说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和内涵,成就了道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司马承祯的艺术才华也让人津津乐道,将道家思想与艺术相融合,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财富。司马承祯受到后世的尊敬和神圣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道教学者之一,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